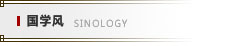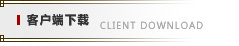转播到腾讯微博
转播到腾讯微博今年(小编按:2014年)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发掘完成四十周年。这次考古发现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其中保存完好的西汉女尸、素纱襌衣等都是国宝级的珍品,而三号墓出土的大批帛书、帛画尤为罕见。帛书共计十多万字,五十余种,另外还有一些竹简医书,为文献中的“书于竹帛”提供了实证,令世人对古代的书写方式和材质有了直观和深入的认知。
简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尚存、已湮没两千余年的古佚书,也有一部分为现存古籍的不同版本。因其为科学发掘出土,抄写年代下限确定,与整个墓葬的关系比较明确,出土时的样态、位置都保持得比较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由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华书局三方合作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出版,是对马王堆简帛文献出土四十年来整理和研究的最佳总结。这项工作是在1970年代以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和湖南省博物馆的帛书整理以及马王堆发掘报告对遣册等资料的整理的基础上,吸收了新出研究成果,全面整理并完整发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所有简帛资料。
在《集成》出版之际,《上海书评》采访了主编裘锡圭先生以及整理团队的刘钊、陈剑、郭永秉、程少轩诸位老师,由他们代表全体整理人员畅谈了六年来的整理心得和体会。裘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跟随唐兰、张政烺、朱德熙等老先生参与了出土文献整理工作,如今在他的带领下,一批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乃至八〇后的学者正将出土文献研究整理工作的薪火接传下去。

马王堆简帛整理团队合影。前排左起刘建民、郭永秉、刘钊、蒋文、刘娇、裘锡圭、董珊,后排左起周波、顾史考、广濑薰雄、陈剑、邬可晶、程少轩、施谢捷。
裘先生,想先请您谈谈这次全面重新整理马王堆简帛文献的概况。
裘锡圭:我们整理的都是老东西,马王堆出土至今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当年出土时帛书全都泡在水里,破损比较严重。虽然近些年来涌现出许多竹简资料,但外界要求马王堆文献全部发表的呼声一直很高,因为这么重要的文献这么多年见不到全貌。整理工作从七十年代开始,其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跟大形势也有关系。这次重新整理,名义上我是主编,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我们中心的年轻人做的,他们才是主力。我们中心的年轻人非常难得,他们对这份外人眼里看起来很枯燥的工作充满了感情,并不仅仅当它是一个饭碗。他们的整理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所以我感觉选择我们这个团队来承担重新整理的工作是很正确的。
但是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我们还是没能按照预计的想法做好工作。一方面跟我国的领导方法有关系,一个单位如果没有大的项目支撑就根本生存不下去,所以我们又要上课又要搞科研完成项目,没有办法全副精力投入到整理工作上面去;另一方面就是环境限制,你看我们这个书的扉页上印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样的项目都有时间限制,如果晚了就没有钱了,所以出版社非常着急,我们压力也非常大。这样的项目完全是硬性操作,只抓时间,不管质量,根本不考虑我们工作的实际情况,这对我们充分利用资料就有很大的限制;还有一方面就是湖南省博物馆压力也很大,他们要在马王堆出土四十年的时候把所有文献整理出版,也很着急。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把碎片多拼合一点,尽可能与原貌接近,注释更详尽一些,但以上诸多因素导致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在前言里也提到了,在资料非常复杂、时间又很紧的情况下,我们屡次推迟交稿时间,已经给中华书局和湖南省博物馆造成了很多压力,感到很抱歉。但事实上还是没有能够在我们的设想下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只能说在环境限制下尽了力,是目前情况下的最好结果了。
您觉得这个团队里的青年学者的优势在哪里?
裘锡圭: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们对这份工作特别有感情,当然也很有兴趣。比如说陈剑,他看到其他人在整理时可能有的字释错了,或者可以拼上一个碎片,马上会和同事分享,没有什么其他考虑或是顾忌。我整理的《老子》这部分也是如此,他先把自己的部分整理好,然后有余力关心我们的部分,不过因为前面说到的时间限制,他关心《老子》整理的时候,图版已经排好了,所以他后来又拼上了不少碎片,就只能够在注释里体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我现在年纪大了,加上青光眼严重,工作效率很低,吃了晚饭基本上就不能工作了,所以我赶《老子》甲本的注释赶得很苦,乙本是无论如何来不及了,所以乙本的注释由郭永秉承担。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投入了全副精力,完成了工作。所以全部文献整理完之后,我最大的感想是,这些工作要换一个单位可能很难实现。
七十年代整理出土文献的时候您大概是最年轻的学者吧?那时的风气和现在比怎么样?
裘锡圭:那个时候可以说风气也是很好的。我那时年轻,精力当然比现在好。一起整理的有我的老师朱德熙、张政烺先生,还有太老师唐兰先生。当时我主要不是负责马王堆,是整理临沂汉简。我跟现在的陈剑老师大概比较像,如果对其他部分的整理有意见,也会马上提供给他们,没有太多顾虑。那个时代是很特殊的,之前刚批判过资产阶级法权,书印出来都没有个人名字的,只有单位名字,就是不让你有个人名利思想。当时不许讲个人名利,倒不是说当时人思想觉悟就高了,不得已而已。现在人热衷于争名夺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这里的青年同志能做到踏实工作、互相帮助批评建议,我就感到比当时更可贵。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项目的主编都是挂名的虚职,不做具体事情,我们这里不是这样。比如像刘钊是中心主任,作为编委也参与整理和注释的工作;我是主编,也负责了《老子》的整理注释工作。我们在一起讨论前言、凡例等很多问题,大家都很积极地贡献建议。不过也有遗憾,要按照我以前的工作习惯,当主编的话肯定要把所有整理好的文献都看一遍,但现在自己的部分都管不过来,就无暇他顾了。
还要提一点,中华书局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和进度,尤其是责任编辑石玉,工作非常细致,每次我们有改动他都很耐心。而且这次的《集成》印得很朴素,还是实事求是的,是给搞学问的人用的,就是定价有点贵。现在有很多关于出土文献的书,材料只有一点点,但是印得很豪华,这样不太好。
以前没有电脑,检索手段也很有限,如果碰到没有传世文献能够相对应参照的出土文献,一般怎么处理呢?
裘锡圭:我们当时古书读得都不怎么熟,得先把简或者帛上的内容看得比较熟悉,然后感觉它大概跟哪些古书关系比较接近,然后把这些古书找来通览一遍,看到跟简文有关系的段落,就摘抄下来。唐兰先生、张政烺先生他们对古书比较熟悉,可能不会像我这样。现在有电脑就方便多了。马王堆出土的文献虽然佚书居多,但很多词句说法是有来源的,能够和传世文献对照。
陈剑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帛书的情况,以及这次的重新整理有些什么新的发现?
陈剑:马王堆帛书出土的时候是存放在一个漆奁里面的,漆奁有五格,长方形的格子上面有两捆竹简,取竹简的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帛书,当时用细铁丝做成钩把竹简钩出来的时候,就把下面的帛给戳破了。下面这些帛有的是卷轴的,还有的折叠成长方形的方块。古代的帛有固定幅宽,一般是四十八厘米左右,帛书有整幅的有半幅的,半幅的一般就卷在木片上,这些帛层层靠在一起,时间长了上层的墨迹会印到或渗到下层,形成反印文,反印文对释读工作很有帮助。
出土的半幅帛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整幅帛,放在漆奁里。整幅帛多数采取先左右折叠最后上下折叠的方式(极少数先上下叠),最后折成十六开大小的一摞(少数有再折一次的情况),保存在漆奁另一个较大的方格里,出土时就像泥砖一样。出土以后用氮气密封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揭裱,先要泡在清水里利用自然浮力让最上层先漂起来,慢慢一层层揭开。
这次整理之后,我们对帛书所用帛的规格和使用方式有了比较清晰全面的认识。一般用来抄书的帛会有几种固定大小,有时候用长的帛抄了短文章,后面留下空白,不会裁去,就一起折叠了,这样空白部分会留下较清晰的反印文,《相马经》和《五星占》是最典型的。通过反印文也新认出不少字和拼上不少碎片。
我们这次还花了比较多的精力研究“衬页”。“衬页”的概念以前陈松长先生写过文章,认为是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空白帛夹在折叠好的帛书中间,用来保护页面;但现在通过反印文和折叠方式复原的研究,衬页应该本来是完整地和整幅帛一起折叠的,面积一般是其一半,后来才跟正文帛片一样断裂成若干片。帛书常年泡在水里,墨迹是从上往下印、渗的,整张衬页摊开后会发现有的是反印文在正面,有的是在背面。这是比较简单的情况。还有全长十二块的整幅帛,衬页揭出来不是六块而是八块,也就是说它当时折叠的时候长度超过了一点(很可能它是为更长的帛书准备的,但最后用在了比较短的帛书上),超出部分也就一起折在中间了,这张衬页我想了很久才想通。而且我们整理时使用的数码照片,情况并不单纯,有时候两张粘连的拍在一起,比例就不一样,正文帛片和衬页总的块数也需要据此加以重新清理。衬页有时候还会裱反了,因为它揭开时背面粘上了下层的部分正文,装裱师傅就可能会把衬页的背面裱成正面。
在重新拼缀上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各篇都不同程度地有新的拼合或改拼。
刘钊老师整理的医书部分好像调整比较多?
刘钊:医书里的《五十二病方》是我们这儿的日本学者广濑薰雄整理的,我整理的主要是《杂疗方》和《胎产书》,后来我把《杂疗方》给分开了。原来整理者把两种书给误合为一种了,分开以后一种是谈房中术的《房内记》,还有一种叫《疗射工毒方》,就是古时候传说的一种虫子叫蜮,在水中含沙射人的影子,让人得病,《疗射工毒方》讲怎么治这种病,有点儿像巫术。我就谈谈几点感想吧,一是,在汉代的帛书上,你会发现中医的一些基本理念、观点或者说体系在那么早的年代就已经确立了,《五十二病方》里有后世的医学分科,非常齐备。方技里大量使用了各种药,现在中医研究借用了很多马王堆的成果,用于临床,据说有些还是很有效果的。它还包含一类叫祝由方,古代有祝由科,像萨满教跳大神似的,口中念念有词,念咒语,行法术。这当然是迷信的装神弄鬼,但现在看来也有它的科学成分在里面,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心理疗法,调动病人自己的潜能。另外这些医书跟三号墓墓主和南方的地理位置都有一定的关系,整个受南方道家影响很深,讲究养生,包括房中术也是作为养生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体操,你会感到当时人对性的观念还是比较开放的。不过医书这部分内容,我感觉现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一方面是文献本身还没有读透,里面有种割裂,我们搞出土文献的平时注意字词,对方技里面这些药性、药理不太懂,好多搞中医的,懂药性、药理、经脉,但文献本身读不通。这两者的沟通衔接还不是很顺畅。
三号墓墓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将军,这些帛书就是他生前的私人藏书,有很多与他身份相合的特征,受南方道家影响深,注重养生,还有众多跟兵法有关的书。当时他们跟南越国接壤,经常打仗,所以有很多地图、天文、占卜的书都跟打仗有关系。
裘锡圭:我们这里的这位日本学者很不错,整理非常细心。
陈剑:《五十二病方》已经是之前研究很多的文献了,广濑这次新拼、改拼了五六十片,整个释文面貌变化就非常大,行数这些完全都变了。
刘钊:我观察过,广濑在食堂吃饭,从来不剩一粒饭,汤也全喝光。也就是说他不喜欢吃的东西也会吃掉,绝不浪费,常年如此,这个很厉害。
可否请程少轩介绍一下数术类文献的整理情况?
程少轩:古代数术曾被视作封建迷信的渣滓,因此马王堆数术类文献在七八十年代帛书第一次整理时并未发表。后来,大家认识到数术文献在科技史、文献学等方面的价值,才开始陆续整理发布这批材料。由于这些帛书有的残损非常严重,有的字迹模糊不清,加之涉及不少专门知识,且在传世文献中缺乏可供比勘的内容,整理难度较大,所以迟迟没有完整公布。此次整理由董珊、王树金、刘娇、刘建民和我负责,大家在学者们过去三十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将马王堆数术类文献整理完毕,《阴阳五行》甲乙篇、《出行占》《木人占》等过去没有完整公布过的材料终于可以展现全貌了。此次整理还是有一些新得的,大家在帛书拼缀、文字释读等方面均有不少收获,对文献本身也有一些新的认识。比如,我们发现《刑德》《阴阳五行》诸篇是相互关联的,较晚的几种抄本是根据较早的文本陆续改编扩充而成。再比如,《刑德》的有些内容是根据实际战例,如楚汉彭城之战、汉军讨伐陈豨战役等编写的,兵阴阳书的编纂者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占辞进行调整。这丰富了我们对早期数术文献的认识。当然,由于整理难度大,时间也非常紧迫,此次整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比如我负责的《阴阳五行》甲篇,在拼缀、释读等方面尚有不少问题,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郭永秉有些什么感想?
郭永秉:我负责的部分之前的整理基础都比较好,除了协助裘老师的《老子》甲乙本工作之外还负责《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我个人的感觉是,七十年代的整理水平相当高,我们现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缀合、释读、断句上有一点小的突破。整个大的框架还是当年那批学人搭建的,至少在我整理的这些方面,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现在有电脑,看反印文比较方便,但我通过整理发现他们当时也是充分看了反印文的,不然有些地方很难拼对。可惜他们当年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技术条件,也可能时间比较紧,有时候遥缀会错行,有些残片清理时有遗漏,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裘锡圭:当时整理《老子》的确是催得很紧的,因为有中央领导要看。
郭永秉:我缀上《老子》一些残片以后,陈剑老师后来看又缀上好多。我们去崇明、茅山等地开研讨会,我真的感觉长进很多,学到很多,我们这个团队互相的感情和学术上的信任感通过这些研讨会得到很大的增进。我记得很清楚,去崇明开会时,我自认为《春秋事语》整得还可以,结果陈剑老师看了一晚上,又有新的缀合和释文改动。裘先生说我们团队的氛围和七十年代差不多,互相有点较劲的良性竞争。陈剑老师对各篇的拼合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经常说他拼帛书像吸毒一样有瘾的。
陈剑:嗯,有人问我老拼来拼去拼碎片干嘛,因为有些碎片拼上去对释文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周易》里面的“休復”两个字右半边在那儿,已经可以知道是什么字,我在残片里找到了左边的单人旁和双人旁,把它拼上去,这才真正“休(修)复”了。我就是尽量把碎片拼上去,减少一点儿,没法儿去问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我只能说,能拼上去为什么不拼呢?就是时间还不够,不然还能多拼点。当然还有些工作是要把本来拼错的拆下来,有的地方真是装裱得天衣无缝的,以前一直就以为是在一起的,但看了反印文之后才发现接合的地方字对不上。
最近十几年出了那么多简,应该对释字、拼合之类的工作有很多帮助吧?
郭永秉:陈剑老师为了整理马王堆,已经把秦汉墓葬里出来的简(除了西北简)全部摸了一遍,对字形非常熟悉。不过易地而处,如果把我们放回七十年代,没有任何便利条件的帮助,白手起家,恐怕也做不到那么好。我非常佩服的是,《战国纵横家书》里面有两处错简,可能从简本抄过来时抄错了两支,没有任何标记的,但整理的时候他们把位置移正了。裘先生说大概是马雍发现的,这是很厉害的。
裘先生,您以前写过一些关于《老子》的文章,对其文本和思想肯定有通盘的考虑,这次整理文献结合了许多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裘锡圭:新想法我打算专门要写文章的,可能不是几句话能概括。举个例子,“宠辱若惊”可能是“宠辱若荣”的误读,我已经写文章讲过了,不过这不是从帛书里来的,是从郭店简里来的。这很有可能是有意的误读,跟道家学派后来的思想变化有关系。庄子本人是不要当官的,很坚决,当然不会有老子为了治理天下而要去为下、受辱的思想。《老子》里说,好的统治者要能“受邦之垢”,坏的事情都由他承担,所以要“宠辱若荣”;他也不觉得什么屈辱都是好的,“知足不辱”,就是说懂得满足就不会觉得屈辱,这里的“辱”肯定是他反对的。庄子讲的是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放,主张独善其身,不屑于当官,但是到他的后学,就不太行了,于是有“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这就给自己留了一条路,跟后来的山林隐逸有点接近了。就算治理国家,也不要伤自己的身,要贵身、爱身,这与“宠辱若荣”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宠辱若惊”可能是庄子后学改的,改得似通非通。
《老子》的面貌很多地方是被后人误解的,过去一般认为因为时代最近,所以《庄子》书里讲的老子最可靠,就没有考虑到古人为了自己思想上的原因加以篡改的情况。其实并不一定是最早的引文就最可靠。
中西方学者对如何释读出土文献的步骤方式有很大的分歧,很多先秦文字在隶定时候写法不一,中国专家认为是某个字,释文就直接写成该字的楷书;但是西方学者在释读时不倾向往传世文献上靠。鲍则岳提过:“我们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要尽最大可能准确地、不含糊地释写原写本里的文字字形,决不能因为作释文的学者本人或其他任何人的假想、偏见或主观决定而对原写本的文字进行增、改或添加。也就是说,释文应该是准准确确、不折不扣地反映原写本的文字原貌,而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您通常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平衡?
裘锡圭:西方有他们的校勘学传统,但任何学问都不能死板地去看。中国古文字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异体、通假等现象,花样很多,一定要根据某种原则去如何处理往往是行不通的。西方人总是觉得他们的学问比我们完整,有一套一套的说法,好像显得很高明。不过这也难怪,因为他们对汉字本身了解不够,只能拿一些方法来生搬硬套。
陈剑:表面看来好像这是方法严密不严密的问题,实际上是他们对于古汉字和古汉语本身的知识不够。如果他们达到水准线以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古怪的说法。
马王堆的地理位置是楚国故地,好像楚地的出土文献特别多,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裘锡圭:马王堆的确是从楚地出土的,但现在出土的楚地文献中有很多抄本有齐鲁文字的特点。从书的原产地来说,也有很多本来并非楚地的,比如《周易》这些并不是楚地自己的文化系统。那为什么楚地出土文献最多呢?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不够全面,很难去确定地回答。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南方比较潮湿,马王堆帛书出土的时候全部泡在水里,好处是隔绝了空气。北方地下没有那么干,半潮半干是最麻烦的,帛和简都很容易腐烂,如果埋在北方的地下恐怕很快就没有了。那么定州的竹简是怎么留下来的呢?是因为那座墓在古代就烧了,竹简碳化了,才留了下来。所以出土文献跟自然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西北甘肃等地出了很多汉简,那是因为干燥,简埋在地下等于自然脱水,这些简出土就不用像南方的简那样要进行脱水处理。
陈剑:有句话叫“湿千年,干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
裘锡圭:我们不能确定的是,用书作为陪葬品的现象是不是楚地要比北方更盛行,因为北方出土的资料还不够。
(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11月2日第B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