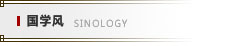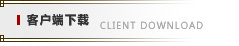您当前的位置:中国古典文库 >>
国学风
民国名人与民国广告
作者: 来源:天津日报 发布时间:2014年12月23日 8:57:36 点击数:979  转播到腾讯微博
转播到腾讯微博
 转播到腾讯微博
转播到腾讯微博
由国庆先生是位兴趣广泛的学者,于风俗、饮食、市廛、游戏、语言等方面都有涉猎,特别是对老广告的研究,成绩卓然可观,已印出《老广告》、《再见老广告》、《和古人一起读广告》、《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诸作。近日,国庆新著《民国名人与民国广告》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我写点读后感受,也将此书推荐给读者。
如今广告已成为一门学问,不少大学都设广告专业,不但有广告学教授,还招博士生,可见这是与时俱进的学问,也是前景很看好的学科。我对广告知道得很少,正像我一点不懂医道,连江湖郎中、赤脚医生那点知识也没有,无可奈何,只能从一个普通广告受众的角度,随便谈谈对广告的认识。
“广告”一词是外来语,源自日语“広告”,传入中国并开始流传大概已在清末,至于表述现代理解的广告含义,那就更晚了。其词虽无,实已久存,当商品交换市场出现,应该就有广告。《易·系辞下》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相传这还是神农氏时代,既有集市贸易,广告就应运而生,大凡有两种情形,一是招幌,二是市声。招幌,即实物性质的广告,《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晏子语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酒帘在先秦时已很常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市声则包括叫卖吆喝、韵语说唱、器乐音响等,相传最早的是姜尚操刀卖牛肉,《楚辞》有“师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扬声后何喜”(《天问》),“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离骚》)。韩非说的“自相矛盾”,自然是广告史上的典型,而伍子胥“吴市吹箎”,则吹奏成调,声音悠扬,不啻是广告史上的一大进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道:“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子胥吹的是箎,后人也有写作竽、筦、箫的,吹箫或许更晚,虽然《诗·周颂·有瞽》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那是宫廷内瞽者奏乐,不是叫卖,郑玄注道:“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那应该是汉代才有的事。
上述都是先秦广告的案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广告的传播样式越来越多,接受层面越来越广泛。时至如今,更进入广告大潮汹涌的时代,满目皆是,充耳皆是。由于广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就被学者所关注,建立起这个学科,专业著作也层出不穷。但一个学科的建立,开始总会有点不完善、不成熟。我看过一本广告史,将军队的旗纛作为悬帜广告,将烽火台的狼烟作为警示广告,将青铜器、瓦当铭文作为标志广告,将告示、榜文、碑刻等作为政治广告,这些自然都是“广而告之”的,但是否可以算作广告,还是很有疑问的。如果依此类推,凡雕塑、牌坊、路牌、寺塔都是公益广告,出丧的白幡自然是殡仪广告,死囚身后插的斩标,也应该叫做行刑广告才是,那就太宽泛、太滥汜了。如果要将广告作为一种学问来研究,就要界定它的范畴,明确它的概念,这应该是广告学者们首先要关心的问题。
我的兴趣不在广告学,然而广告记忆了历史,记忆了时代,闲来翻读杂书,那些记录着古人日常生活内容的招幌和市声,就常常让我怦然心动,让我走进那已非常遥远的历史生活场景。
就以敝乡来说事。北宋时,朱勔父亲朱沖是个串街叫卖日用物品的小贩,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记道:“朱勔之父朱沖者,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物博易于乡市自唱,曰常卖。”至于朱沖唱卖些什么,今已无从考证了。乡贤范成大晚年居住城内西河上,他将听到的各种市声记入诗中,《自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有曰:“巷南敲板报残更,街北弹丝行诵经。”“菜市喧时窗透明,饼师叫后药煎成。”“朝餐欲到须巾里,已有重来晚市鱼。”夜来卖卜人在深巷里经过,叫卖声凄凉悲切,《夜坐有感》曰:“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欠明朝籴米钱。”苏州城内河道成市,小贩一边摇船一边唱歌叫卖,《咏河市歌者》曰:“岂是从容唱渭城,个中当有不平鸣。可怜日晏忍饥面,强作春深求友声。”他更有《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啼号升斗抵千金,冻雀饥鸦共一音”之咏,令人感慨低回。明清苏州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大都市,广告业十分发达,康熙时人章法《苏州竹枝词》咏道:“酒担豚肩匝地过,香甜柔脆到门多。五簋一点挑来卖,不买些吞待若何。”自注:“其物可欲,其香触鼻,其涎直挂。”可见那叫卖声往往会惹起听者的食欲。嘉庆末佚名者作《韵鹤轩杂著》,卷上说:“百工杂技,荷担上街,每持器作声,各为记号。修脚者所摇折叠凳,曰对君坐;剃头担所持响铁,曰唤头;医家所摇铜铁圈,曰虎撑;星家所敲小铜锣,曰报君知;磨镜者所持铁片,曰惊闺;锡匠所持铁器,曰闹街;卖油者所鸣小锣,曰厨房晓;卖熟食者所敲小木梆,曰击馋;卖闺房杂货者所摇,曰唤娇娘;卖耍货者所持,曰引孩儿。”苏州商品包装,很早就采用仿单,需求量很大,都由年画铺承印。《点石斋画报》记载了一个“赛行致病”的故事:“苏垣尧峰山施某与同村人马某相善,日前万寿圣节期内,闻城中灯景之盛,马自夸捷足,与施约曰:‘愿限二刻往返六十余里,违则倍罚,能则汝以英饼一枚酬我。’施诺之,对准日晷,奋步疾行,不逾时而焉已归来。施以为诳,马出城中稻香村茶食示之,凡稻香村售物必印日期于纸裹之上。施见其非妄,如约酬之,同赴酒家买醉。甫入座,马即口吐鲜血,一息奄奄,施大惊,急延伤科某医,索酬多金始肯施治,戏真无益哉。”那是光绪二十年六月德宗生辰前后,苏城举行灯会。尧峰山马某向施某夸口,以二刻时间去苏州并返回,赌以英镑一枚,马某真如“神行太保”,但归来时已累得吐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由“稻香村售物必印日期于纸裹之上”一句,可见当时稻香村的仿单上,已印有茶食生产和销售的日期。
凡此种种,都是苏州的昔年烟景,正因为有这样具体的细节,就会觉得这一道道消逝已久的风景,仍然是亲切的存在。知堂在谈到闲园鞠农的《一岁货声》时说:“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投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深深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这种民间生活史料,历来不受重视,也很少有人去关注,知堂在介绍约瑟夫·阿狄生等写的《伦敦的叫卖声》之后说:“我不知道中国谁的日记或笔记里曾经说起过这些事情,平日读书太少实在说不出来,但如《越缦堂日记》、《病榻梦痕录》等书里记得似乎都不曾有,大约他们对于这种市声不很留意,说不上有什么好恶罢。我只记得章太炎先生居东京的时候,每早听外边卖鲜豆豉的呼声,对弟子们说:‘这是卖什么的?natto,natto,叫的那么凄凉?’我记不清这事是钱德潜君还是龚未生君所说的了,但章先生的批评实在不错,那卖‘纳豆’的在清早冷风中的小巷里叫唤,等候吃早饭的人出来买她一两把,而一把草苞的纳豆也就只值一个半铜元罢了,所以这确是很寒苦的生意,而且做这生意的多是女人,往往背上背着一个小儿,假如真是言为心声,那么其愁苦之音也正是无怪的了。”可见广告并不完全是物质交流的需求,其间含有非常丰富的民俗意蕴,且由此反映出人间的情感。
国庆这本《民国名人与民国广告》,提供了民国时期人物和广告的故实。辛亥以后是广告史上的重要转折期,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过渡,梳理、记录、叙述这一时期的广告现象,乃是丰富的社会生活史料,况且又以人物牵出故事,使得这历史场景更加鲜活灵动。这本书既可作为广告学的辅助读物,也可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琐碎,那是社会史、经济史、风俗史等专业著作不能替代的。正因为如此,它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上一篇文章:文化2014:盘点中国出台的那些文化禁令
下一篇文章:研究高鹗是中国文化史如何对待文化名人的问题


Copyright(C) 2011-2015 杭州国文科技有限公司 新华电子音像出版社 All Right Reserved.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浙杭西字第00839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浙网文[2015]0210-030
浙ICP备11003728号-1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浙B2-20110142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浙杭西字第00839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浙网文[2015]0210-030
浙ICP备11003728号-1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浙B2-20110142